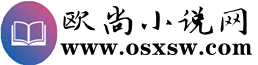房超英站在浦东白莲泾的小马路时,太阳刚刚从东方地平面升起,晨光将不远处的世博演艺中心的银色飞碟大楼涂抹得如同星际穿越归来一般,斑斓却又苍凉。宽广得甚至带些空旷的世博园区地块,如同新生的婴儿,在晨光的触摸中惺惺然睁开眼睛。
上海世博会已经结束几年。这块曾聚焦过全国目光、聚集过二百多国家和地区建筑与文化的土地回归平静时光,因平静,甚至显得有些寂寞。
有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片现在看似空旷的土地,默默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居民。
时间如灰,不动声色地掩去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痕迹。
在搬离这块土地时,房超英也以为,自己终于真正逃离那段令她窒息的生活经历。可随着年岁渐长,这片旧居越来越多地回到她的梦里。特别是面临重大抉择之时,这种梦回便更加频繁。
她慢慢明白,那些被拆除、被平整的房屋并没有消失,它们和那些消失在时间深处的岁月一样,只是换了个存在的方式,从土地上搬入了每个老居民的脑海中。
世博会征地搬迁前的浦东白莲泾,是房超英的老屋。
今时这片已被金钱和绿草包装一新的土地上,曾遍布密如蚁穴般的自建房屋。一条条仅容两人并肩而行的小弄堂,如蛛网般将这片居民区分成一块块不规则区域。弄堂两边,片片密布矮小逼仄的房屋。这些房屋都由两层构成。房屋上半部可以看到残旧的木质结构和窄小的玻璃窗口,仔细看,在窗框上方,还悬挂着几块灰色蛛网。下半部则杂乱地堆放着许多家常用品。旧家具、小煤炉、带柄铁锅,缺轮子的儿童车杂乱地挤在一起;一只大脚盆倚靠在墙角,上面还倒扣着一张褪色的竹椅。
在弄堂中间,常常有穿着拖鞋的、打着赤膊的中老年男人常常团团围坐成一圈,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谈笑。在他们身后,矮小妇人提着马桶低头前行。那木质马桶应该十分沉重,妇人因为提着吃力,身体还向另一侧努力倾斜着。
在妇人旁边,一名中年男子站在一幢二层房屋边,正在仰头向上传递一捆青菜,在二楼敞开的窗户内,一个略略有些暴牙的妇人向下探出半个身子,便能轻松接过那捆青菜。房屋的低矮程度,可见一斑。
在房屋拆迁前,摄影师将这里的某个瞬间拍成黑白照片,被收藏进一本叫做《上海世博回顾展》的画册。房超英从画册上翻拍了一张,存在自己手机里。
照片上,择菜老妇身后那间矮小拥挤的砖木房,就是她的家。在那里,她如一颗发育不良的黄豆芽一般,弯弯曲曲地沿着房屋内昏暗而又拥挤的缝隙成长,一直长到如花似玉的二十岁。
房超英的名字有个小故事。在她出生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向国际社会响亮地喊出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宏伟口号。一些初为人父母的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将那几年出生的孩子取名为“超英”或者“赶美”,与之前的“建国”“抗美”“援朝”,之后的“文革”“红卫”遥相呼应。
她叫超英,小她两岁的妹妹叫赶美。房超英成年后,一直对这个男女通用的名字十分不满,但一直没有办法弃之不用。一直到结婚后,才在小姐妹的指点下找到解决办法:改户口。在婚后办理户口迁移时,她将“超”字去掉,并将带有时代特色的“英”改成了具有女性浪漫气息的“莺”。
这样,她就拥有了两个名字,婚前认识的邻居同学都叫她房超英。婚后结识的同事朋友都叫她房莺,或者阿莺。
超英、赶美出生时,家中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从房超英有记忆起,两个小女孩的活动范围,就局限于由两张条凳搭成的临时床铺上。
临时床铺太窄小,窄到如果两个小女孩大动作翻身,轻则人跌下床,重则连床也翻掉。而她们的床翻掉后,便会惊醒睡在一旁的哥哥姐姐。哥哥还好,姐姐一旦被吵醒,等着她的肯定是一番数落,然后,便是爷爷奶奶带着苏北口音的呵斥声,接着,一定会传来隔壁邻居用拖把杆用力敲墙板的咚咚声……
很多次,幼年房超英都会惊恐地捂住耳朵,等待本就十分破败的房子在那嘈杂的吵闹声中轰然坍塌。可是一直没有。
一直到上海世博园征地动迁前,这原本就是父母当年为栖身而匆忙搭建的房子都奇迹般地屹立在一群同样破烂的棚户房中,并为兄嫂、姐姐姐夫、侄女侄女婿、外甥夫妇分别争取到一笔数目不小的动迁款和位于三林世博家园的安置房。
房超英至今仍然能清楚地描摹出自己当年所居住的那片方寸之地。
没错。她当年的家,的确可以用“方寸”来计量。在成人举手便可触顶的、仅十八平方米的房屋内,拥挤地居住着祖孙三代八口人,后来,哥姐又先后在这里结婚并带回来另一半。白天还好办,总会有人不在家中,房间内也显得不那么逼仄。夜晚,当所有人都回到家中,睡觉,便成了考验持家者智慧的最大难题。
对于这个难题,房家父母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在他们的主持下,已成家者的床之间用布帘相隔,尚未成年者便与饭桌、竹椅轮班。待全家都吃完饭、桌椅全部收起后,他们的被褥才从各处搬出,放在临时搭起的“床”上。
可就在这窄小的几乎没有任何隐私的小空间内,阿哥阿嫂的女儿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众人眼皮底下孕育并诞生。这让已经成年的房莺每每回想起来,总有一种不洁之感。
这不洁之感不仅仅来自于一张没有隐私可言的床,还来自于人类最原始的需求——吃喝拉撒中的如厕问题。
房超英家中也有马桶,但是父母明确规定,这马桶只能给行动日渐不便的爷爷奶奶专用,凡是可以独立行走的孩子,小便可以,大便都必须与大人一样,到小区活动中心的公共厕所排队解决。
房家所处区域,与她家格局一样的家庭有近百个。需要到公共厕所解决问题的有数百人,而社区文化中心的公共厕所每天早晨五点才开门接客。
清晨内急,想及时解决问题,除了随地方便之外,方法只有一个:早起排队,排在队前端。
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奇观。在被称为远东第一大港的上海、在以精致、洋气、文明而闻名于内地的大上海,在黄浦江东岸一片灰旧的棚户区内,每天天还没亮,便有一群身着睡衣、脸上带着睡意的男男女女守候在小区活动中心厕所的门外,焦急地等候厕所开门。
1990年,中共中央下达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政令之前,这与浦西只有一江之隔的土地,沉默地生活着许多与房家处境相同的居民。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这些居民又根据各家男女主人的出生地再次分出层次。
房家,便处于精神层次的最底层。尽管生在浦东、长在浦东,但在房超英幼小的心中,并未认可自己上海人的身份。每每与邻居小囡吵架,对方怒极时,也常以“江北人”称之。
老辈上海人对苏北人的轻视,岂止在言语中,简直渗透到骨头缝里。
房家来自苏北一个小乡村。在房超英出生前,父亲与其他乡邻一样,因贫穷告别家乡,乘一叶细长小舟,载着全家老小和所有家当,一路沿苏州河摇浆而上,寻找可以生存的地方。来到黄浦江东岸这片尚未开发的土地,不知是谁先停下了前行的脚步,下船搭建出第一间棚户,然后,陆续有其他怀着相同目的到达此地的船民们也纷纷停船不前,踩路筑屋,渐渐地在白莲泾一带形成一个独特的居民群落。
一代代人出生,一次次搬离。渐渐地,留在这里驻守的,都是无力离开或者固守家园不愿离开的人。
房超英父母都是老实人,父亲生前是码头搬运工,母亲则在一户户不断因时代而更新换代的各类新贵家中帮佣,一直工作到六十五岁行动不便才回到家里。
十二年前,房超英薄有积蓄后,曾给了母亲一笔不小的钱款,想让母亲到浦西买套房子,过过真正上海人的生活。但老太太一直以住不惯新村为由推脱。
寄托了房家长辈“福至运达”厚望的长子房运达一辈子都在穷困线附近兜圈,倒是在老母亲去世后盼来了“好运”。十年前老太太去世,临死前,她将这笔钱和房产平均分给生活条件比较困难的大儿子和大女儿。
本想凭母亲的遗产过几天好日子,但是,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已经嫁给日本人并移民的四妹房赶美专程回国,要求哥哥姐姐将父母的房屋和遗产全部拿出来,四个人平均分配。在已经富裕的房莺表示愿意放弃遗产分配后,大哥房运达、大姐房跃进、小妹房赶美三人,连同三人各自的配偶、子女,还有子女的配偶和子女,十几口人挤在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天天吵、摔、砸。
吵闹了一个月后,见哥姐始终不肯拿出母亲的财产重新分配,日籍华人房赶美愤然雇请律师,将房运达和房跃进告上法庭。
对于手足间的官司,从头到尾,房莺都脱身事外,不置一词。在女法官判决前对涉案当事人进行例行调解时,也淡淡表示,自己只是来看看判决结果,没能力帮助法官调解几人的矛盾,更无法调和几人因财产而破裂的亲情。心底的话,房莺哽在喉咙口没有说出来:各自生活近三十年,四人之间的亲情早已因为鲜于联络而淡漠,除了同用一个姓氏,在手足脸上,她看不到一点让她产生温暖回忆的东西,有的只是疏远他隔离。
对于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而言,家有几个小孩算是常态。家境富裕者,尚可感受到手足友爱,寒贫家庭资源有限,想要长大,想要长好,只能想尽办法从手足那里去争。
房超英记得,有段时间,母亲收工回家前,哥哥都会主动跑到巷口去迎接母亲。当时仍然健在的奶奶常常夸奖大孙懂得心疼姆妈,但刚刚四岁的房超英感觉并不那一回事。因为每天母亲和哥哥一起回家后,两人都是一脸压抑的笑意。
这种情况维持了大半年后,实在抑制不住心中好奇的房超英在母亲收工前就早早候在她帮佣的那户人家门口,想看看母亲和哥哥究竟有啥秘密。
晚饭时间后,那户人家的门开了,母亲连连说着“谢谢侬”,双手合在胸前,略弯着腰从门内淡黄的灯光中退了出来。候着对方将门关了,这才直起腰,踩着急匆匆的小碎步向家走去。
房超英跟在母亲身后急走。她惊奇地发现,不管母亲走得多急,她的双手一直合抱在胸前。就在这时,哥哥房运达一脸兴奋地出现在巷口。
“小精豆子,小心肝,快过来。”母亲欢快地向哥哥伸出手臂。手心,是一个又红又圆的大苹果。
已经十二岁的哥哥快步迎上去,轻车熟路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递到母亲,母亲快手快脚地削好果皮,一切两半,母子俩便一人一半,低头啃了起来。从背后看,两人的肩胛骨都一无例外地因为瘦削而向上高耸着,顶得衣服上突起四团尖尖的小包。他们啃食的嚓嚓声,连巷口处偷窥的房超英都听出了其中的急迫和贪馋。
那是1967年。那一年,四岁的房超英每天都感觉饥肠辘辘,每次要手上多出几道筷子打出的红印,才能从妹妹手中夺一块饼或者一块馒头。那又红又圆的苹果,她只在店铺的橱窗里看过,别说吃,就连摸都从未摸过。
可是,眼前那一幕,却没让她产生向往,而是一种被背叛后的气愤,气愤中带着恶心。比床板高不了多少的房超英以惊人的耐心连跟了母亲三天,三天中,相同的一幕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上演。
若干年后,已经老迈的母亲和子女们一起回忆她当时帮佣的那些人家。对于其中一户革命军人家庭中的男主人,已经有些老年痴呆的母亲竟然仍旧记忆犹新:“那个衣领上戴两面小红旗的蒋先生呀人最好了,每次帮佣结束,伊都会递给我一个大苹果,那年月,啥人家才能吃上苹果哟……”
长大后的房超英盯着母亲看,当年的背叛感再次泛起。可母亲单纯而又傻气的笑容又让她恍惚:当时所看到的那一幕到底是真还是幻觉?
当然不是幻觉。在觉察到母亲和哥哥吃独食的秘密后,房超英趁哥哥不注意,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那把削铅笔用的小刀,愤恨地丢进公厕粪池里。那一种由于背叛而带来的恨与绝望,母亲可以忘记,富有后的房莺可以忘记,作为房超英,她无法忘记!
为了忘记这种由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厌恶感,从四岁开始,房超英就不再吃苹果。
……
房莺从年幼回忆中抽离,向着东方地平线直直伸出左手,尚未完全喷薄而出的朝阳停留在手掌上方,真像当年母亲手心那只红苹果。
房莺的脸皮抽搐一下,将手掌,慢慢合拢,捏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