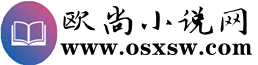走出来梦的时候,已经过了7点。就是说,这呀那呀的与希早子说了近两个小时的话。
心想好冷啊,再仔细一看,路上有点湿。随着从有山的方向刮来的硬质的风飘舞着白色的东西——是雪。
希早子搓着戴着手套的小手,突然对我说想看看我画的画。
“这倒并没有什么关系。”我暂且表示了同意,“不过,还是下次再说吧。”
“为什么?”
“又是晚上,而且刚才你也说了,最近这一带好像挺不安全的。”
“时间还早呀。”
“公寓有没有关门时间什么的?”
“因为是学生公寓,所以没有关门时间,而且这公寓就在你家附近,走十分钟左右,又刚好是回家的路上,俗话说趁热打铁嘛。”
“去一个不熟悉的男人家里,好吗?”
“怎会呢。你不是那种危险人物吧?”
“这可不知道。”
“绝对不是那种人。我只说一下就领会了嘛。挺敏锐的,这样看上去也……”希早子信心十足地说道,随即把手掌伸向落下来的大雪花。
“不过,”我一面心神不安地望着她那看去天真烂漫的面容,一面说道,“还是改日吧。”并非有理由无论如何得拒绝,只是说来有点夸大其词,我还没有将年轻女子邀到家里的精神准备。
“那说定啦。”她有点失望似的说道,“下次一定要给我看呀。”
途中与希早子肩并肩走着。一路上,她讲了自己的事情。
听她说,她从小喜欢画画,本想上美术大学学日本画的,但她其他课目的成绩非常优秀,所以周围呼声就很高,说那样太可惜了。就是说,何必上美术大学呢,“好大学”不论怎么样都可以进。
好像父母也反对。她的父亲是当地某银行的董事,他非常讨厌女儿“热衷于艺术”。结果,她就屈服于这种压力,考进了Kxx大学的文学部。
“至今我还时常后悔,心想自己意志太薄弱了。”当时她感慨万端地说,“不过,我也没有自信自己那样有画画才能。”
“才能什么的,那是很含糊的话。”不知为什么,我情不自禁地这样说道,“俗话说,喜好能生巧,我想那才是真的。如果真的想画画,就是干着其他什么事也能画,判定这样画出来的作品是好是坏——对它的评价什么的,和画的本质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对真正喜欢的事、想干的事,只要有充分的信心就行。”竟然能流利地冲口说出这种话来,虽然也心想这不该是自己说的话。
“不过,我想你还是有才能的,架场也这么说。”
“那是一个看了我的画之后才能决定的问题吧。”
“不,不是那种评价的意思……”
而且她说出了飞龙高洋——我的父亲的名字。好像这也是从架场那里听来的。
“不知道我父亲怎么样,但我这个人,确实是个微不足道的人。”——这是心里话——“只是利用他留下的财产,自满自足于画画而已。从社会上的人来看,是个到了这个年纪还闲呆着的不可救药的男人。因为至今还没有自己挣过钱嘛。”
“钱什么的,我想那才是两码事呢。”
“这呀,是你对艺术这东西的信仰使你这么说的。”
心想这话又说得太过火了,说出后,我当然深深陷入了自我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