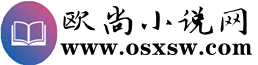“她俩旅途劳顿,下去休息了……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张居正终于不再揪着“姑姑”那个问题不放,张佑有自己的想法,办事也有一套自己的准则,他只是好奇而已,并不想管的太多。
再退一万步讲,就算张佑真的喜欢李妍又如何,只要明威伯的正室夫人是名门闺秀就成,其余的,就算他讨十房八房的小妾,人们也只会艳羡,便有不满的,也不过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罢了。
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张佑的未来,他如今拥有的一切来的太容易了,朝野上下,嫉妒眼红的人多,盟友知交却太少,根基浅,偏偏做的却都是得罪人的事,圣眷优渥倒也无妨,万一哪天没了圣宠,可就太危险了。
要是有个进士的功名就好了,他相信,凭借张佑的聪明才智,再加上自己的打点,一甲不敢保证,考个二甲登科总是没有问题的。
可惜呀,打从太祖爷开始算起,还没听说过哪个伯爵参加科举考试呢。
没有这个正途出身,也就难怪申时行潘季驯王国光他们瞧不上张佑了。
张佑可不知道张居正动了这么些心思,嘿嘿一笑:“父亲有所不知,密云新来的这位康县尊是个妙人儿,开头的时候跟孩儿辩了半天,我还以为他也是那些道德至上的清流一脉,谁知道骨子里却是您说的那种循隶,务实的很,居然跟孩儿想在了一处,也想在密云建个水库……”
“等一下,什么水库!”张居正惊讶地打断了张佑。
“咦,兰琪跟玛丽没说吗?玛丽新发明出一种建筑材料,颇有些神奇之处,我早就有心在这边建个水库,正好用得上,就把她带过来先看看……”
张居正不落痕迹地皱了皱眉头:“怎么想到建水库了?”
“这不是见老百姓饱受干旱之苦嘛,放着潮河白河不利用起来,岂不太浪费了?”说着张佑将自己的设想详细的跟张居正说了一番。
“这么大的工程,你自己的财力怕是担负不起,而是需要申报朝廷吧?”
张佑点头一笑:“正有此意,这不跟您商量嘛,刑部尚书潘季驯是治水能臣,工部曾省吾听说对于治水也颇有见解,这两位都是您的门生故吏,如此利民之举,只要您说句话,还不立马通过?”
张居正忍不住苦笑了一声:“子诚啊,你想得太简单了,听为父给你算一笔账,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十万民夫不多吧?按每人一天十文钱算,一天需耗费百万,折合成银子的话,每天最少千两,给你按最快的速度完工,两年,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全部算下来,也得七十多万银子,这还是为父最保守的估计,真要干起来,怕是百万两也不够。这还仅仅是人力一项,材料费,运输费……一样一样算下来,绝对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字(其实用天文数字合适,可惜说话的是张居正),其目的,却仅仅是一县或者数县的百姓,你觉得,朝廷能愿意出这银子么?朝廷不出的话,你自己又如何担负的起?”
一番长篇大论说下来,张居正有些喘不上气,张佑则犹如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有些不甘心的说道:“也不是白白付出啊,只要水库建成,最起码周边数县的收成还是可以保证的吧?咱们就少算点儿,一年十万赋税,有个十年二十年的,怎么也能收回成本了,这还不算其它的收入……”
“你可别说水库里养鱼养虾这话,就算形成规模,一年下来能有多少?”张居正歇过气来,再次苦笑道:“曲高和寡啊,满朝上下随便挑,能有如此远见的一巴掌就能数过来。”
“看来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张佑终于认清了现实,失望的叹了口气,没办法,这年头的人思想太僵化,把持朝政的那些大佬们又太自私,修建水库这种费时费力费钱还没有多大利益的事情,他们是不可能同意的。
“就是可怜密云那些百姓了,我已经让康丕扬准备告示,征召民夫……”他的语气十分沉重,叹了一口气,将后面的话咽回了肚子里,站起身来:“我有点累了,回屋躺会儿。”
“唉!”这和当年的我何其相似啊,但有此心者多矣,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个呢?这么多年,我殚精竭虑,气象好似一新,其实呢,不过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罢!为富不仁者仍旧为富不仁,食不果腹者照旧食不果腹,改变了什么呢?不过就是华发早生,空留遗憾而已!
“父亲,哥哥没事儿吧?”张若萱有些担忧的问道。
“受点挫折也好!”张佑答非所问的说道,接着回望一眼神情怔忪的女儿,默然片刻,幽幽再叹:“推为父回屋吧,为父也有点累了。”
…………
张佑确实身心俱疲,躺在床上,却根本就睡不着,回来多半年了,他仍旧看不透如今的人都是怎么了,没有信仰,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一如他看不透后世的那些人一般。
有真心希望大明好的人吗?当然有,比如张居正,比如戚继光,比如朱翊钧,这样的人还是有很多的,可是更多数的人,还是将大部分心思都放在自己的前途以及切身的利益上边。
他们才不管大明的未来会如何,自然更加不会去关注百姓的疾苦,指望这些人让大明强大起来,无异于痴人说梦。
自己的力量还是太弱小啊!
要是能把发电机研究出来就好了。
心烦意乱,他干脆起床,谁也没叫,独自一人出了别府,漫无目的的闲逛起来,不知不觉,居然来到了城隍庙--不知为何,朱氏皇朝十分重视这个城隍爷,每一个县城都有一个城隍庙,而每一个城隍庙,又几乎相当于集市的代名词。
已是午后,赶集的人早已散了个七七八八,一道略有些熟悉的身影吸引了张佑的注意,那人身穿青布长袍,正在从跟班儿胳膊上挎着的大篮子里不停的往外拿馒头,依次递给他面前跪着的那一溜儿头插茅草,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的孩子们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