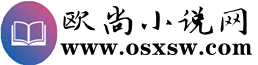“还能做什么打算?本帅都已经被万岁爷调到蓟州了……本帅现在只想再做几年,然后告老还乡,回铁岭安安生生的做一个富家翁。”
“恩帅万万不可如此消沉,您手下那么多弟兄可还指望着您呢,再说了,树欲静而风不止,铁岭可是在辽东呢,您在辽东经营多年,想回家安度晚年,怕是不太现实吧?”
李成梁眼睛内精光一闪而逝,叹了口气:“不然还能如何?人为刀俎,只能是听天由命罢!”
“恩帅,您的根基在辽东,只有那里才是您应该待的地方。”
“可本帅如今已经被调到蓟州了,你以为本帅不想留在辽东吗?”
“其实也简单,只要让万岁爷认为,辽东非您不可,到时候不用您申请,他自己就把您调回去了。”哈奇意味深长的说道。
李成梁的眼睛眯缝了起来,拍了拍哈奇的肩膀:“你果然没有让本帅失望!”
亚尔弗列德终于回来了,带回来了足足数十车的红薯和玉米,这是一件足以改变大明历史进程的事情,所以,张佑,十分认真地将这一天记了下来--万历九年(1581)七月初一,这也是他穿越到明朝整整半年的日子。
张居正在密云疗养,冯保在昭陵当掌印,邢尚智去南京做守备太监,张鲸死了,戚继光和李成梁对调,未来的司礼监掌印陈矩如今已经成了坤宁宫的管事牌子,能否当上司礼监掌印还是两说……
一切都在按照张佑的意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让他很欣慰,因为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
玉米和番薯没有进张府就直接从通州的运河码头运往了密云,在那里,有良田千顷在等待着张佑创造奇迹。
不过仍旧有烦心事,闵廷甲和魏允桢申请关闭遵化铁冶的奏折被驳回,加上李成梁退缩,没有激起多大风浪便归于平静,但紧接着闵廷甲就上了一道题本,以十分激烈的严辞弹劾正在《明报》火热连载的《神雕侠侣》鼓吹师徒不伦之恋,宣扬暴力,思想恶俗等等十余桩罪状(熬夜写,实在想不出来其它的罪状了,有能想出来的欢迎留言),申请朝廷将其列为禁书,同时追查作者金庸的真实身份,严惩不贷……
这让张佑想起了后世的一些见闻,某国产影片难得票房好一点,便引来无数专家学者怒怼,什么思想不健康啦,暴力血腥啦,没有考虑对未成年人的感受啦,甚至直接上升到人身攻击……
当然,那些人是崇洋媚外,见不得国家好(当然更多的还是为出名),和闵廷甲不同,不过其恶心程度倒是不分伯仲,着实让张佑腻歪。
不过,这也给了他反击的借口,很快,明报上就接二连三的刊载了多篇署名金庸的文章,什么《驳通政使闵廷甲》,《再驳通政使闵廷甲》啦,什么《论文学作品的存在意义》啦,什么《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啦,一篇篇文章就如同一枚一枚的炮弹,很快就在朝野之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反对者有之,支持者有之,继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辩。
也就在这个时候,《明报》报社忽然公开刊载了一则消息:即日起,本报社公开对外征收稿件,不限文体,一经选用刊载,稿酬从优,欢迎各界人士来稿。
内容通俗易懂,字里行间,一如既往的加着人们已经渐渐习惯的标点符号,虽然有些词语十分新鲜,可所有看到这则消息的人,仍旧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这下好了,正愁没个好的争辩地点呢。再然后,当第一篇稿件被采用并且收到了丰厚的稿酬之后,读书人的热情被彻底的激发了出来,一时间,代表双方观点的稿件如雪片般飞进了《明报》报社,《明报》成了他们的战场,不见血腥,却有刀光。
继发行当日热气球投递之后,《明报》再次火了,火到就连大街上的贩夫走卒都在不停的议论着从上边听来的最新战况--
“听说了吗?闽大人也往《明报》投递文章了,名字叫《回某太学生书》,里边写着什么‘吾心皎皎,日久自辨,尔等昏昏,不见黑白”……”
“什么角角黑白的,心上还能长角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昨天不是有个署名‘太学生’的指责闽大人沽名钓誉危言耸听了吗?闽大人这是在说自己的心如同天上明月那般皎洁呢。”读书人模样的插嘴卖弄。
嘘声一片,有人道:“文邹邹的真没劲,还是金庸的文章听来痛快……呃,当然,要是我闺女敢跟我提什么爱情自由,我非打断她的腿不可!”
这话引来一片哄笑,连旁边一身便服的张佑听了也不禁莞尔。
“你还笑,都是你闹的,你看看,这几天都乱成什么样子了?”兰琪女扮男装跟在张佑旁边,见他跟着笑,不禁随口抱怨了一句。
张佑轻嘘一声,不再偷听,边往前走边道:“乱点好,沉寂的太久了,我就喜欢这种热闹。”
“少爷,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要是将来你有了闺女,你会让她自由恋爱吗?”钱倭瓜问道。
“为什么不呢?”张佑反问,声音略高了一些,适才插话的那位读书人不禁向这边看了过来。
“可是,万一要是她看上了一个叫花子呢?”钱倭瓜不依不饶的问道,这一下,连刚才那位声言只要女儿敢爱情自由就打断她腿的汉子也停下跟另外一人的争执看了过来。
更多的人注意到了主仆之间的辩论,张佑见状,索性停了下来,于是很快他们的身边就聚了一大帮人。
“你觉得我的女儿会看上叫花子吗?就算看上了,那也肯定是那个叫花子有什么过人之处,不过是暂时蒙尘而已。”
“听这位少爷的话,好像瞧不起咱们叫花子嘛,咱们怎么了,不偷不抢,比大街上那些混混们以及官场上那些蛀虫们强多了。”一位穿的破破烂烂,却颇有些气势的中年人朗声插话。他的手里拿着一根竹棒,肩上挂着一个褡裢,上边五颜六色,缝着八九条布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