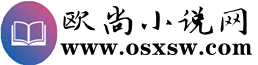甘婧看到赵闽时,已经是被送入南汇中心医院的第三天。
为了让甘婧能更好地休息,主治医生在静脉注射药物中加了安眠成分,最初三天,甘婧都是在半梦半醒中煎熬。
在疼痛难忍之时,甘婧不停地喊着爸爸妈妈,可意识稍稍清醒,她便拼命阻止要给她妈妈打电话的护士,“我妈有心脏病,不能受惊吓,你们给我请个好点儿的护工就好了,我大小便可以自理,不用麻烦人,请个护工帮我看着药水瓶,帮我打个饭就好。”
赵闽看到甘婧时,她头脸上伤口缝合处的肿胀仍未消退,左手臂骨折处打着厚厚的石膏,眼神也有气无力。
“婧婧,你受苦了。”赵闽看着甘婧的眼睛,难过地说,“我来晚了。”
甘婧示意护工帮她将床摇起一些,让自己半坐着,待护工出去后,甘婧才有些困难地笑着说,“你来啦。医生说长头发会影响伤口治疗,就将我的头发剪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现在很丑吧。”
赵闽微微摇头,“对不起,婧婧,让你吃苦了。”
甘婧回答,“医生说我额头上可能会留下伤疤,以后好了只能留长流海遮一下了。”喘了口气,甘婧急迫地问,“你去过公安局了吧?他们把房莺抓了吗?如果她不认,她家地上、沙发上、地下室都有我的血,可以验DNA。警察来了好多次,可他们只是问我情况,却没人告诉我他们的进展如何。”
赵闽坐在甘婧的床头,仔细看了看甘婧头上的伤口,小声说,“放心,检察院已经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了房莺。”
甘婧长吁出一口气,点点头,“那就好。”
停顿片刻,甘婧小声说,“在我被她关进地下室之前,那个女人对我说,赵魏祺已经死了。”
赵闽叹口气,“警方又重新调查了当年曾和魏祺有过接触的纳士员工,他们都证明说最后一次看到魏祺时,唐红果儿还和他在一起。而在魏祺失踪前后那段时间,房莺陪何其多在外地谈项目,并不在上海。”
甘婧想了想,“那何其多怎么说?”
“他说当时他的确与房莺在外地谈项目。他还说,他小孩又病了,要回美国去处理家事。”
甘婧一下子瞪圆了双眼,“他走了?他不能走。”赵闽笑了笑,“放心,他现在被警方以配合调查为由暂时限制出境。来,你累了,先躺一下。”赵闽走到床尾,动手将甘婧的床慢慢摇下。
“对了,你上次说的发现了纳士经营方面的问题,是怎么回事?”甘婧慢慢躺下,小声问。
赵闽摇摇头,“这是小事,等你好些我们再聊。”
甘婧叹了口气,“上次你就说纳士经营方面的问题是小事,等有结果再告诉我,结果我差点和你永远地告别了。”说着,甘婧拉赵闽衣袖,“还是告诉我一点吧,好吗?”
赵闽笑了笑,细心地给甘婧牵了牵被子,这才缓声说,“纳士的经营情况如何,说真的,我一点都不放在心上。我现在挂心的,是你的身体。”
甘婧睁着青肿未消的眼睛,有些吃惊地看着赵闽,“是不是医院告诉你说,我除了破相之外,还残疾了?”
赵闽忙换上一副笑容,小声安慰道,“别紧张,你身体正在好转。我的意思是,医生说啊,那个女人下手太狠,让你的肾脏也有了问题。不过,为了最大可能减小因康复所带来的伤害,他们要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确定是否要做手术。”
说到这里,赵闽的脸色微变,“上帝保佑。幸亏你身体素质不错,普通人流了那么多血,再被关在零度左右的地下室内30多个小时,早就支持不住了。”
甘婧看看二十四小时悬挂在头顶的输液袋,叹了口气,她想起在半梦半醒中,右肾脏的确一直剧烈疼痛,但因为全身的伤处都在痛,她并没有多想。
“我已经将你的一整套病历和这边的治疗方案传送到我美国一位医生朋友那里,刚刚他来过电话说,你年轻,修复力强,如果自我修复好了就不用摘除。明天他就亲自飞过来,再给你诊疗一下。所以你要好好休息,配合治疗。”
“美国的医生也能到中国来诊病?”甘婧问,“医院同意吗?”
“同意的。医院的大门,在面对复杂疾病时,是对所有医生开放的。”赵闽看看甘婧青肿的脸,突然苦笑了一下,“你真是个傻丫头,从别墅里逃出来时就剩下半条命了,还没忘记把房莺的作案凶器也带出来。警察说,他们接到保安的电话赶到案发地时,你已经深度昏迷了,可还死死地握着那根高尔夫球杆,急救医生和护士两个人都掰不开你的手。”
“我主要是为了防身,我被打怕了。”甘婧不好意思地笑。
“你睡吧,我静静陪你一会儿。”赵闽有些心酸,他将手轻轻放在甘婧的眼睛上,让她休息。
甘婧闭上眼睛,听赵闽的声音缓缓在耳边响起,“我给你申请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顺带着换了一部新手机,那里面已经存了我的电话号码。其他你想要的电话号码,等你好些后自己导进去。不想再联系的人,就忘记他们吧。”
甘婧想睁眼睛回应,被赵闽轻轻按住,“不要动,好好休息。”
甘婧吃力地笑了一下,表示感谢。
赵闽声音低低地,“魏祺失踪这两年多,我一直认为他是去了某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创作或者是散心,从没怀疑过他会遭遇不幸,更没怀疑过他身边的人。谢谢你,给我指了一条正确的路……”
赵闽的声音很低,手心很暖,在难得的平静中,甘婧感觉血液中的安眠成分慢慢腾腾发散开来,不知不觉,竟然睡去。
一个月后。感觉自己恢复得已经相当不错,甘婧打电话通知了妈妈。
接到电话从武汉赶到上海,黄淑兰还没坐稳,就被查房换药的刘护士说了两句,“你是21床的妈妈?我们还以为她是孤儿。”
甘婧忙坐起,用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的右手臂挽住刘护士的胳膊,笑嘻嘻地解释,“刘姐姐,我妈不知道我住院的事啦!我怕她着急,就没告诉她。”
黄淑兰显然没料到女儿竟然会伤得这样重。接到甘婧的电话时,她还以为甘婧只是跌了一下,可能会伤到筋骨,因此,但当她看到甘婧吊在胸前的左手臂和头顶仍然留有伤疤的嫩红色伤口时,吓得一把捂住嘴,没哭出声音。
看着甘婧妈妈哭了,责任护士哼了一声,叮嘱甘婧要定期复诊,端起小托盘出了病房门。甘婧伸手从房头小柜上抽出几张纸巾递给妈妈,又向她旁边的男人问了声好,“张叔,你也来啦。”
被称为张叔的男人点点头。
甘婧父亲去世五年后,黄淑兰和这个同样丧妻的男同事登记结婚。对于这个瘦小、苍白的继父,成年后的甘婧一直保持着最大程度的礼貌,却无法建立父女之情。
“你坐一下唦,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再和你张叔去办理出院手续。”哭了几分钟后,甘婧妈妈去病房内的洗手间洗了把脸,红肿着双眼扶起甘婧,让她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好,又返回病房给甘婧收拾个人物品。
“这花还要不要?”甘婧妈妈指指床头柜上的漂亮花瓶,扬声问门外的甘婧。
自从赵闽来过后,每天清晨,他在上海的助手都会安排鲜花公司给甘婧送来一小束带着露珠儿的鲜花。甘婧想了想,起身回到床房,从花瓶里摘了一朵尚未开放的粉玫瑰花苞握在手心,指指剩余的花朵说,“就让它们留在这里吧,送花的人看到它们,就知道我已经病愈出院了。”
甘婧妈妈点点头,将甘婧的个人物品归置好,又将甘婧扶到长廊长椅上坐好,这才拉着丈夫向走廊另一头的电梯走去。
甘婧的妈妈接近一米七零,与甘婧高大健壮的爸爸站在一起很般配,可是与身边这个瘦小男人相比,却显得有些高胖。在武汉街头,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中年夫妻并肩走在一起,留给人温馨但又略显突兀的背影。
看着一高一低、一胖一瘦两个背影消失在电梯中,甘婧微笑了一下,将目光投向窗外。在病痛中盘桓了一个多月,不知不觉,上海的春天已经来了。入院时还光秃秃的枝干,如今已经萌出婴儿牙齿般的瓷白小芽。
一周前。外部伤势已经明显减轻的甘婧正在病床上半躺着望向窗外发呆,刚刚得知到她入院消息的百合、蓝祖平、魏元、正夫、洪杰和眉眉一起来探望她。看着几乎与床单混然一色的甘婧,众人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为了打破尴尬气氛,甘婧道,“我看着不是不很吓人?我们再编一部僵尸大战剑齿虎的脚本,我可以本色出演怪兽。”
“艾玛!快别提剑齿虎了。”洪杰叹了口气,摇头说道,“咱们费的那些心血,可能要浪费了。”
“怎么了?你们不是已经去西部园区进行过现场安装与调试了吗?”甘婧不解地问,“技术方面又有新问题了?还是对方认为故事脚本还要改动?”
蓝祖平轻咳了一声,面色晦暗地说,“都不是。那个,甘婧,你还不知道吧,你知道了也别放在心上。剑齿虎主题公园又延迟开园了。啥时候能重新再开还是个未知数。”
“为什么?”甘婧问。
蓝祖平回答,“听说是两方的项目负责人都涉嫌经济问题。环宇那边的哥们儿说,去年前任佟董跳楼自杀后,剑齿虎项目本来已经被新佟董叫停,是我们何总给了项目负责人白小姐一笔巨额活动经费,白小姐才游说佟仁义重新启动这个项目。佟仁义不爱钱,惟一的喜好就是肤白女孩,白小姐和何其多联手给他奉送了好几个白雪公主才打动他。”
“甘婧,我估计白小姐和何其多当时也想把你当成炸弹去炸佟仁义的,佟仁义对你也蛮喜欢。幸亏你没上钩。”眉眉小说声,“要知道,面对一个又有豪车又有豪宅还有豪气的男人,很少会有女人不动心的。”
“那倒是。”百合笑了一下,“甘婧,说实话,那佟仁义对你又是豪车接送、又是共进晚餐的,你真没动心?”
甘婧瞪了百合一眼。
“那你出事后,他来看过你吗?”百合又问。
甘婧摇摇头,伸手去拿水。可能是动作太大,她腹中突然一阵疼痛,情不自禁地捂着肚子露出痛苦表情。
“怎么了?”百合弯下腰,担心地问。
“医生说房莺把我的肾脏打伤了。”甘婧吸了口气,又努力笑了一下,“不过,医生说我身体好,不用动手术什么的,自己可以慢慢痊愈。现在好多了,只是偶尔会痛一下。”
“真看不出,房莺这女人这么狠。”魏元摇摇头,倒吸一口冷气。
“是呀,你第二天没来上班,艾米说你突然辞职回老家了,还让行政部将你的东西收拾好放进小会议室,将你的位置空出来。”蓝祖平接到,“那天正好是我们从西部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当时还追问你为什么会突然辞职,艾米说她也不清楚,你是向何总直接提出辞职的。”
“我们想打电话问问你情况,如果是真的,就给你举行个告别会,可你也不接电话。”眉眉接着蓝祖平的话说。
“后来再打,你手机就一直关机。”百合说。
“那之前十多天,我的电话就被他们偷偷给停机了,你们打的其实不是我的手机。而是他们重新申请的卡号。”看众人面露不解之色,甘婧解释了一下,“在我们准备去西部出差前,估计房莺通过行政部拿到了我的身份证,将我手机办了停机,然后重新申请了一张卡。这样,我的手机和卡都在,但其实已经没有用了。你们打电话时接通的是她手里的那张新卡。”
说到这里,甘婧自己都感觉程序太复杂,自己打断了话题,“嗨!这个过程挺复杂,等以后我慢慢再跟你们解释。还是你们告诉我一些公司的情况吧。”
众人沉默地听着甘婧的解释,看到甘婧期待眼神,这才反应过来,百合推推魏元,“当时你在场,你和甘婧说。”
“好吧。”魏元扶扶眼镜,低声说,“大概在听说你辞职的第三天,两名警察来到公司,说要找房莺了解一点情况。”
在接到甘婧报警当天,警方便对房莺南郊别墅进行了初步勘察,并在第一时间来到纳士公司,找房莺调查核实甘婧被囚及受伤情况。
看到警察这么快找到自己,房莺非常震惊。因为不知道别墅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甘婧是死是活,所以一开始,她只是装出很吃惊的样子,想听警察给自己进一步描述一下发现甘婧时的情况。当听到警察说“一个叫甘婧的女青年在她别墅里受了点儿伤”,想请她一起回公安局配合调查时,她知道一切都完了。甘婧没有按照她预先安排的那样死去。而只是“受了点伤”。
“这是告知书,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先在这里签个字。”女警察小声招呼着房莺。
房莺低头看看女警察手中那张纸,又看看她肩头闪亮的警徽,一股绝望之情瞬间弥漫全身。被警察抓回去,结局就一个,房莺心知肚明。
机械地在告知书上签下名字,房莺听话地跟着两人往外走去,等走到办公区门口时,她突然一把将女警察推倒在地,向走廊敞开的玻璃窗冲去。窗台很高,房莺也很敏捷,几乎没费多大力气,就攀了上去。可当她俯身向下,准备一跳了事之际,眼前突然出现的高度让她猛吃一惊:那扑面而来的地面就像灰色冰面,让她还没撞击而上,就感觉到彻骨的惊恐和痛楚。而就在房莺犹豫不决之际,男警察已经追到她身边抱住她的腿,想将她从窗外拉回来。
“真的,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体力这么好。”并不了解前因,仅在现场目睹房莺跳楼拒捕的魏元说到这里,声音都不由从低转高。
听到魏元的大嗓门,甘婧邻床患肾衰竭的张阿姨重重地水杯“咚”在台桌上,“乡下人。吵死人啦。”她嘟囔了一句。
甘婧住的是间条件不错的病房,只并排放着两张床位。甘婧最初入院时,另一张床上住的是一名做肾结石手术的郁姓报社编辑。最初半个月,甘婧因为浑身是伤,在疼痛难忍之时,会在半夜低声哭泣。这位姓郁的阿姨并不嫌弃她吵了自己休息,相反在甘婧神志比较清醒时,她还会隔着两人之间的布帘低声和甘婧小声聊天,讲自己小时候在淮海路生活时的一些趣事和父辈认识的一些旧上海名人。
待甘婧的伤势好转后,这位郁编辑病愈出院。当天下午,姓张的阿姨住了进来。与郁阿姨相比,年纪相仿的张阿姨明显难以相处,而且冷漠。
甘婧连忙向布帘那边赔着笑脸说,“张阿姨,对不起,我们吵到您了。他们是我同事,说几句就走。”
张阿姨哼了一声,不再说话。
被张阿姨一哼,魏元停了下来,将声音调低,“那个男警察伸手抱住房莺的腿,想把她拉回来,房莺发了疯似地拼命踢男警察,男警察一边喝令她老实点一边往下拉她,可硬是拉不动,还被她踢了好几下。看到这种情况,男警察大声喊我们男同事过来帮忙,可——”
“你们不敢去?”甘婧问。
魏元点点头。“幸好女警察冲上去帮忙,两人才将房莺从窗台上扯了下来。房莺双脚一落到地上,就开始打男警察。男警察可能看她是个女的,又众目睽睽的,不太好意思和她动手,稳住身形后掏出手铐想将她和自己铐在一起,可两个人撕扯了足足一分钟,他硬是按不住房莺,还被抓伤了脸。最后还是女警察捉住她另一条胳膊,男警察才勉强给她戴上手铐。”
蓝祖平也吸了口冷气,“当时我们都看傻眼了,现在想想,她可真他妈有劲儿。”
“房莺的确太狠了。看你头上的伤,都一个月了,还没长好。”眉眉轻轻摸了摸甘婧的头上的纱布。
甘婧叹了口气,问,“对了,何总现在怎么样了?”
蓝祖平、魏元几个对视一眼,没有说话。
“何总也被警察带走了吗?”见众人都不说话,甘婧又问了一遍。
“哦。是这样,从房莺被公安带走后,我们也一直没见他。不过估计也凶多吉少。”蓝祖平小声说,“听说当时房莺是从宴请佟仁义的酒席上将你带走的,何总也在,他们关系那么好,应该也是知情者吧。”
“对了,警察不是经常来找你了解情况吗?他们怎么说?”魏元问。
“警察只问我问题,从不回答我问题。”甘婧苦笑。
“警察倒是找我了,”蓝祖平接过话题,“他们找我核实当时我被人抢劫的情况。”
“哦?没听你说过呀。”百合看着蓝祖平。
“不是前天刚找嘛!公司都快解散了,我上哪去找你说呀!”蓝祖平回答。
“公司解散了?”甘婧吃惊地问。
“房莺被公安带走后的第二周,大股东派了一个代表来,说是要各位员工正常上班,工资薪水全部正常支付。”魏元叹了口气,“大股东话说得好听,其实意思就是一个,花钱养着我们,配合公安和检察院的调查。你说他们的调查一结束,那我们还能有什么结局?连老总都进去了,肯定要解散的。我们都在四处面试,找工作。”
“那你找到了吗?”甘婧问。
魏元说,“找到了,我们都是靠专业吃饭的,总有地方要的。下周我就去正式报到了,那家公司也在张江,是家浙江老板开的私企。”
“哦。那也挺好的。”甘婧点点头,心中突然有些伤感。
“先别说公司的事吧。蓝老师,警察找你,不会是告诉你,你也是被房莺打倒的吧?你好歹是个男人呀!”百合好奇地看着蓝祖平,“人家甘婧是个小姑娘,身子弱力气小,你尽管有点瘦,但好歹是个男人,和她一对一对都打不过她?”
蓝祖平面不改色地说,“丫从背后下黑砖,我没机会跟丫对打。再说了,警察都打不过丫,我被丫打倒也不丢脸吧。”
百合疑惑地问,“这女人以前是做什么的?怎么这么大力气?”
“房莺是高尔夫俱乐部金卡会员,还以业余选手的身份参加过亚洲杯高尔夫球赛,房莺曾经炫耀说,她手臂的爆发力很强,一般男人都赶不上的。”甘婧一字一句地说。苦笑一下,她转向蓝祖平,“蓝老师,房莺为什么要袭击你呢?”
“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你刚来公司不久,有一天我和你一起去吃午饭,我不是和你说了挺多关于唐红果儿和赵总的事情嘛。知道了你的事情后,我反思,那天房莺可能听到了我和你的对话,然后对我产生了一些怀疑。她砸我,一是想警告我,二可能是怕我电脑里有唐红果儿或者赵魏祺的资料,索性抢走了事。我算是两朝元老了。以前公司有活动,照片基本都是我拍的。”
甘婧看看手上连接的点滴管,说,“好在她已经被公安抓了。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她所做过的一切,很快都会水落石出。”
九人又和甘婧闲聊了一会,一起向甘婧说再见。蓝祖平迟疑片刻,小声说,“你们先走,我想和甘婧再说几句。”
甘婧看了看蓝祖平,微笑着点点头,挥手向其他几名同事再见。
几人离开后,蓝祖平一脸严肃地站在甘婧床边,用更加微弱的声音说道,“甘婧,我和你说个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秘密。我挨打后,房莺曾经到家里来看过我,给我包了个一万块钱的红包,还说了挺多关心体贴的话。我一感动,就将你和我的对话全部都告诉了她。后来,我们在栖山路宵夜时说的你和唐红果儿是同学的话,我也找个机会对她说了。”
甘婧平静地看着蓝祖平,莹白如纸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我一直认为她只是热衷于打探下属的隐私,从没想过她竟然会对你下毒手。上周得知你差点被房莺打死的消息后,我愧疚得一直睡不着觉。”蓝祖平低下头,认真地说,“甘婧,对不起了。”
甘婧慢慢地从床上坐起来,拉住蓝祖平的胳膊,小声说道,“蓝老师,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一切都过去了。”
蓝祖平摇摇头,从包里掏出一个银行现金袋,塞到甘婧手心,“甘婧,这里是一万块钱。不多。我知道公司没和你签合同,你也没有医疗保险,这点钱,就算一点医药费吧。”
甘婧将那包钱拼命向蓝祖平手里推。蓝祖平一边说收下吧,一边避开甘婧的手将现金袋放到甘婧的枕边,如释重负地叹口气,转身向外跑走。
等甘婧慢腾腾地站起来,拿着那个现金袋、穿鞋走到门口时,那里早已没有蓝祖平身影。
看着手里的白色现金袋,甘婧突然升起一个古怪想法,如果那天自己意志崩溃,或者说此前没有阴差阳错地天天跑步健身,那么蓝祖平他们今天来看的,会不会是一个摆在殡仪馆存放室的小盒子?看到自己化成了灰,心怀愧疚的蓝祖平一定会在夜静更深之时,偷偷找一块僻静之地,将一叠冥币烧给自己。那时候,已经站在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也会像这样捏着一叠钱,无声地望着他的背影吗?
那个世界,会有唐红果儿吗?会有爸爸吗?也会像这里一样,喝口水都要用钱买吗?想到这里,甘婧悄悄笑了起来。
“甘婧,你笑什么?”在甘婧走神之际,黄淑兰已经办好出院手续,与丈夫一起回到甘婧身边。
甘婧吓一跳,忙摇头,“没事,想到马上出院了,挺开心。”
“医院说,你入院后你们单位存了一笔钱在财务室,结账后还有多的,我给你拿回来了,给,总共一万块钱。”张叔递给甘婧一叠有零有整的钞票。
又是一万块钱!甘婧一愣,然后默默笑起来。半晌,她示意妈妈将钱替自己收好,自己站起身来,一步一步,慢慢离开自己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出院回家。
回到熟悉的家中,看着去接待佟仁义那晚匆忙试穿的几条裙子依然在沙发上保持着自己出门时的状态,看着茶几上剩下的半包零食,看着绿色纱帘仍然在窗前没心没肺地轻轻拂动,看着穿衣镜中自己苍白如纸的皮肤,本来心情一直晴朗的甘婧,突然生出一种再世为人的桑沧感。
人在身处灾难中心时,并不会特别害怕。相反,当一切都过去,抽身事外冷静观看时,才感觉恐惧。
“姆妈,前段时间你去我武汉的屋里看过冇?”甘婧问。
“看过。你连被子都冇叠,衣服还挂在阳台高头。我都给你收起来了。”黄淑兰回答。
“知道我为什么不叠被吗?”甘婧问。
“为什么?”黄淑兰摇头。
“我是听老同事说啊,房子不能老空着,会惹东西。特别是床铺,一定要铺着,不然,就会有无家可归的鬼魂来睡的。”甘婧神秘兮兮地放低声音,“他们来睡了,我不就没地方睡了嘛。”
黄淑兰有些吃惊地看看甘婧:“你吓老子滴,真的假的,你莫吓我啊!”
看到妈妈被自己吓到了,甘婧笑得前仰后合,心中却暗暗酸楚,也许,常常出现在自己梦中的另一个果儿,这回真的不会再来了。
待黄淑兰熟悉好住宅环境并张罗完午饭和晚饭后,已经到了睡觉时间。
因为甘婧的腿还不能频繁上下楼梯,在她的坚持下,妈妈和张叔住她二楼的卧室,她住一楼客厅沙发。
甘婧的房间布局并不适合成年的一家三口居住。有时,黄淑兰夜半醒来,会趴在二楼的栏杆上悄悄看着甘婧抹眼泪。甘婧几次想将自己在濒临死亡时见到爸爸甘毅然的情景告诉妈妈,但一见继父一副蹑手蹑脚的样子,便没有说出口。
夫妻纵是情深似海,说散了也就散了,但血缘不一样,从生到死,牢牢跟随。父母肉体死了,音容笑貌依然活在子女的脑海里,随着子女也老去,愈来愈固执地显现在子女的肉体上,一代一代,永不断绝。
半个月后,甘婧执意让黄淑兰回家。
送走黄淑兰,甘婧将家里简单收拾了一下,第一次主动拨通赵闽的电话,“我现在有足够的精力、体力和你见面了,你这几天在哪里?方便见我吗?”电话中,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好的,后天下午三点,在你家小区门口见。”赵闽回答得十分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