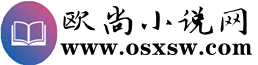赵闽给甘婧带来的,是警方发现的一条线索。
在警方近期破获的一起贩毒案件中,一名一直没被打击过的毒品拆家供出一批从她手中购买过零包毒品的下家。经过警方反复调查核实,这其中竟然有唐红果儿。
“你说果儿生前吸毒?”甘婧几乎叫了起来。
“甘婧,你先别激动。我想问你,你真的了解唐红果儿吗?”赵闽沉声问道。
甘婧有些不甘心地想了半天,才无奈地垂下头。她不了解唐红果儿。甘婧和唐红果儿的旧宅早已变成一片商业楼盘。那个扎着一头小辫子、会跳民族舞的七岁小女孩,也和老家的山山水水一样,成为一段美丽回忆。
二十年的时光,足以凋零一座芝加哥那样的汽车工业老城,也足以繁华一座浦东这样的金融航运新城。更何况一个普通人。
“唐红果儿吸毒,是新型毒品还是海洛因?”甘婧问。
想起初到上海前夜,在长途卧铺大巴上偶遇的那一群惶惶如寒号之鸟的戒毒者,甘婧心中一冷。
“是新型毒品。”赵闽回答。“有一种是专门在Party时吃的药丸。”
甘婧皱着眉头,“吸毒?可是警方给出的尸检结果,并没发现她身体内残留有毒品成分。”
“毒品在人体内也有一个代谢时间。她体内没发现毒品成分,也就是说,她自杀前一段时间并没有吸食毒品。”赵闽接道。“这个问题,我回来后也专门问了专家朋友。”
“你在赵魏祺的个人物品中发现过跟毒品相关的物品吗?”甘婧问。
“没有。魏祺每次出门前,都会把家里收拾打扫一下。他们请的清洁工人会在家中没人的情况下,再来打扫第二次。所以他家中一直十分整洁,个人物品放置得也很规整。也因此,他最初失踪时,我和工人都以为他出差或者出去度假了。”赵闽说。
“赵先生,你说,唐红果儿自杀,以及赵魏祺失踪,会不会与吸毒有些关系?”
赵闽扬扬眉毛,示意甘婧说下去。
“我们来做一种最直接的假设,假设赵魏祺发现了果儿吸毒,十分生气,苦劝之后,果儿一直没能戒断,赵魏祺索性提出与她分手。结果,唐红果儿因为受不住分手的打击,加上吸毒导致她心理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跳楼自杀了。得知她跳楼的消息后,赵魏祺十分悔恨,也……在某种情况下殉情了。”
殉情……
赵闽不易觉察地哆嗦了一下。
“以前我们寻找赵魏祺,一直把他当成失踪,总认为他在某处小住散心,等心情平复了就会回来。如果,他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呢?那找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赵闽苦笑了一下,“你的意思是找无名尸体?”
甘婧点点头,“我知道,让你接受这个观点很难,寻找过程更难。”
“不过……”甘婧犹豫了一下。
“什么?”赵闽问。
“这个假设也有个前提,就是唐红果儿自杀在前,赵魏祺失踪在后。”
“这个很难估量。”赵闽回答。
“赵魏祺住的小区里应该有安保监控系统吧?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摄像头中是什么时候?”
赵闽略一思索,有些迟疑地回答,“应该在唐红果儿自杀前。我记得当时调看过小区监控录像,最后一次看到魏祺,他还是和唐红果儿在一起,两人去地下车库取了车,一起乘车离开。”
“如果魏祺失踪是在唐红果儿自杀之前,那情况就又有些复杂了……”甘婧自言自语。
“海风凉了,我们上岸吧。”赵闽看看被风吹得脸色发白的甘婧,小声地说。
步行上岸,赵闽的私人助理快步迎过来,“赵先生,晚饭已经准备好。”
赵闽点点头,助理向不远处一招手,一辆黑色奔驰轿车稳稳地开了过来。
“上车吧。”赵闽帮甘婧拉开车门,“去我家里吃顿简餐。”
赵闽的公寓位于南汇临港新城一栋灰色楼房内。楼房外表普通,走进去才能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偌大的楼房有四部电梯,每一层楼只有一户人家,四梯只为一户人家服务。
进得门去,赵闽示意甘婧自己随意看,他去换件衣服。
甘婧没有走动,而是站在原地,四处看了看,像所有时尚杂志上介绍的生在海外、长在海外的富人一样,赵闽家中摆放的全部都是红木家具,客厅里处处可见暗红雕栏、莲花、祥云和低眉敛首淡淡微笑的菩萨。而从可以用辽阔来形容的客厅面积看,赵闽的家堪称是豪宅中的巨宅。
“我很少来这里住,都是助理他们帮我弄的。”换好居家服装的赵闽笑着示意甘婧到餐厅就坐。
看着红木餐桌按顺序一道道摆上的西餐,甘婧轻轻笑了一下。
“在中国明清式家具上吃现代西餐,感觉有点怪是不是?”赵闽准确说出了甘婧心中的想法。
“这是一种进步。”甘婧笑着拿起刀叉,“我不太懂西餐礼仪,如果出错了,纠正我没事的。”
赵闽笑着点头。
两人安静地吃完晚餐,赵闽殷勤地邀请甘婧到露台去小坐,他微笑着说,“助理买这幢房屋时,告诉我说这里是湖景房。坐在家中就可以看到滴水湖。因为一直很忙,我还从没上去看过。一起去看看好吗?”
甘婧点头,“我也没看过滴水湖,一起去看看吧。”
赵闽住宅的露台立体种植着许多在冬季盛开的花草,坐在微微拂动的晚风中,竟有花草的清香一阵阵袭来。
不远处,滴水湖像一面镶嵌在大地中心的圆镜,幽幽地反射着湖边灯光。
“他们说,临港新城的规划方案源于德国一家公司,总设计师假设有一滴来自天上的水滴落入大海,泛起层层涟漪。那个湖是水滴,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就是它所泛起的一道涟漪。”赵闽坐在甘婧身边,轻声向甘婧指点着周围的景观,“这工程算是豪华,你看,那个可以观景、行船、游玩的巨大水滴是个完全用人工开挖得来的人工湖。不过,新近填出的那个湖中岛有些破坏整体景观。”
随着赵闽手臂的起伏,他身上散发出微微的温热气息。一刹那间,甘婧心中竟浮现出一丝恍惚之感。赵闽拉着椅子,从她的旁边移到正对面,温柔地看着她的眼睛,轻声说道,“我们一直在说魏祺和唐红果儿,却从没说说各自的一些事。”
甘婧回答,“那你说吧,我愿意听。”
赵闽摇头,要说,“也是Say you say me。不是只听我一个人说。”
甘婧想了想,“那你想知道什么,就问我,你问我答。”
赵闽点点头,“好。能否告诉我你结婚了吗?”
甘婧笑,摇头,又点头,又摇头。
赵闽愣了愣,又问,“你家中都有什么亲人呢?”
甘婧回答,“只有我和妈妈。九年前,爸爸为了救一名溺水的小朋友因公牺牲了。”
赵闽又问,“那你有男朋友吗?”
甘婧侧着头想了想,下决心般回答,以前有过,在省直机关工作,副科级公务员,眼镜男,已经领了结婚证,但没办酒席。因为我执意要辞职到上海来,就悄悄把结婚证换成了离婚证。甘婧有些尴尬地说,上海同事都以为我是单身未嫁女子,其实,我不仅结过婚,而且已经离过婚了。
赵闽波澜不惊地点头,“后悔吗?”
甘婧点头,“后悔了。”
“嗯?”赵闽看着甘婧,“后悔离婚吗?”
甘婧苦笑一下,“我后悔和他在一起时,没有对他和他家人好一点。离开武汉的最后半年,因为我的原因,我们一见面就吵,然后就是冷战。再见面又吵,再接着冷战。最后一次见面,他低着头,微微含着胸,脸上是绝望而又无奈的神情。当时没有感觉,可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感觉对不起他。他是公务员,我可以一走了之,压力和质疑,他要一个人面对。”甘婧叹口气。
赵闽也叹口气,“你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而他要沿着原来的路线走,结局也只能这样。”
甘婧深深口气,挤出一个笑容,“轮到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赵闽点头,“好,你问我。”
甘婧问,“你太太为什么不和你一起回来呢?”
赵闽回答,“她要在家里照顾三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走不开。”
甘婧哦了一声。
赵闽仍然期待地看着甘婧,等她发问。
“我没问题了。”甘婧低下头。“不早了,我要回家了。”
赵闽愣了愣,半晌才重重叹口气,起身让司机备车。
低头上车时,赵闽伸出手,轻轻放在甘婧的头顶。感受到甘婧的僵硬,赵闽抽回手,微笑示意甘婧坐好,自己敏捷地钻入车内,坐到甘婧身边。
赵闽并不知道,他手掌带来的战栗,一直到很久后,才从甘婧的心头散去。
回家的路上,甘婧情绪有些低落。沉默了几分钟后,她才将话题转回到赵魏祺的身上。甘婧没有再谈如何寻找赵魏祺的尸体,而是转换了一个一直困扰她的问题:纳士公司为何要刻意隐瞒唐红果儿死亡和赵魏祺失踪的事实。
“哦,是我不让何其多宣扬的。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知道的人总归越少越好。”赵闽回答。
“可是,就在我向一个资深员工打听唐红果儿的事情后不久,那个员工下班回家后就被人打晕抢劫了。而我也被莫名其妙地喂了安眠药,还在医院里住了一天。”
“喂安眠药?怎么回事,你怎么从没有跟我说起过?”赵闽坐直身体,吃惊地瞪大眼睛。
甘婧详细将那晚情况向赵闽描述了一下,末了,吸口气说道,“幸亏那时我还不认识你,手机中没有你的电话,只有一张唐红果儿与赵魏祺的合影,要不然,那晚我挨的可能就不是一记闷棍了。”
赵闽双眉紧锁,思索着什么。
“你认为这两件事都和唐红果儿的死亡有关?后来有人主动问过你唐红果儿的事情吗?”赵闽问。
“有。就是被抢劫的那名员工。叫蓝祖平。我解释了,说我和唐红果儿是同学,我也是到纳士后才知道她曾经在这家公司工作过。还有,我感觉,房莺一直对我有种病态的防备和反感。如果不是我在剑齿虎项目中还有点用,何其多还算需要我,她早就找个借口将我赶走了。”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赵闽问。
“您看,我到纳士工作快一年了,他们一直连个劳务合同都没和我签,与我一起进入公司的几个员工都签约了。作为一家已经在上海这个法治相对完备地区运作了四五年的合法企业,这是不正常的。”甘婧说,“还有,每次我一和蓝祖平这些老员工走得近点儿,房莺就非常紧张。”
我听何其多说,“房莺是个能干女人。为公司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他离不开她。”赵闽笑笑,“那女人我见过几次,不太像是能用手段吸引男人的类型,我想,应该是工作能力确实很强吧。”
“她是吸引不了男人,但可以按倒男人。”这话到了嘴边,甘婧又咽下去。这话与两人讨论的事情无关,她也不想给赵闽留下一个低俗形象。
“可能,她是出自女人的第六感,对你有着天生的不喜欢吧。青春将逝的女人都有这种第六感。毕竟你年轻漂亮。”赵闽笑着说。
“说到第六感,我倒想起一件事。”甘婧接道。“那还是我刚刚参加工作之时。我和一位曾获得过许多国家荣誉的老刑警聊天,我问他屡破大案的秘诀是什么,他告诉我,主要是靠第六感。他说,在各种摄像头还没布满整个世界的时候,一有大案发生,他们在做完现场勘查后,第一件事就是以最快速度确定侦查方向,特别是追捕方向。下这个判断,就是靠第六感。”
“人的第六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赵闽接道,“但是,有时并不准确。”
“是的。对了很好,一旦错了,兄弟们就要多走好多弯路。由于那位老刑警的第六感特别准确,所以错的时候很少。后来我慢慢明白,他所说的这个第六感,是靠知识、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与判断力综合而来的。”
甘婧顿了顿,看看一脸疑惑的赵闽,沉声说,“房莺的第六感,也绝非老女人对年轻姑娘妒忌这样简单。”
“你认为她有问题?”赵闽问。
“凭我并不经常准的第六感判断,她与唐红果儿的死,一定有着某种关系。我甚至怀疑,当时打晕蓝祖平、给我的水中放安眠药的人,就是她。”
“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赵闽问。
“我不知道。”甘婧摇头,“不过,我有办法试探出她到底是不是当时迷晕我并偷走我手机的人。”
“不要。”赵闽断然制止甘婧说下去,“不要做任何事。对她产生怀疑可以,我来想办法。中国是法治社会,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
甘婧看看赵闽,“您知道中国每年的失踪人口数量有多少吗?中国的警力又有多少吗?警察不可能有那么多精力找回每一名失踪者。我们现在对房莺只是怀疑而已,无凭无据的怀疑,警察也不会采纳的。”
“我有办法处理。总之你太太平平的,不要涉险。”赵闽打断甘婧的话,闷声说道。
甘婧学着赵闽的样子耸耸肩,不再和他争辩。
车行至一半,赵闽电话响起,是行政助理打来,告之赵闽,何其多的小儿子生病入院,这几日返回美国处理家事,可能无法在国内与赵闽见面。公司运营情况,请三位副总向赵闽汇报。
赵闽低声说好,挂了电话。
甘婧脑筋一转,突然想到一个方法,“赵先生,以往您作为大股东来听纳士汇报,都采取什么方式?”
“听汇报、看材料。”赵闽回答,“纳士是魏祺的心血,他在时,我听汇报什么的也只是走走过场,并不真的看和听。”
“我有个小建议。”甘婧说。
“你说。”赵闽看着甘婧。
“您这回听汇报,带一名精通财务的下属去。从审计的角度认真查查纳士的经营情况。”
赵闽笑,“小丫头,你的想法我明白的。但你知道吗,纳士从创立起就有着十分完善的企业财务审计制度,不仅有内审,每年年底,还会请知名会计事务所进行外审。何其多他们给我看的材料中就有非常完善的财务审计报告。就算他们敢造假,负责外审的会计事务所也不会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帮他们造假的。”
甘婧低头想了想,感觉赵闽的话有理,但又与自己的想法有些差别。
眼见自己的住所已经出现在不远处,她有些焦急地说,“我不是财务人员,不太明白审计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得,国内曾经有不少企业负责人因为经济问题落马,在问题暴露前,他们的企业也一直在进行着不比纳士业余的内审和外审。我不管您用什么方法,反正我希望您利用大股东的身份仔细去查查。房莺这边我查,纳士经营问题,您查。”
说完这句话,甘婧向赵闽一挥手,起身下车。
甘婧还没走上几步,就被赵闽一把拉了回来,他低头盯着甘婧,十分认真地说,“我再重申一次,你不要再做任何事。纳士实际经营情况和房莺的个人情况我都会想办法查。听到了没有?”
甘婧感觉手臂有些疼,便本能地向外拉,一回头,看到赵闽紧绷的脸上全是担忧的神情,眉毛也拧在了一起,不由笑了起来。
看到甘婧的笑容,赵闽的表情也慢慢松弛,他松开手,认真地说,“甘婧,你笑了,就表示你听懂并认同我的意见了。我是个守信的人,我也希望,你信守现在对我的承诺,太太平平上班下班,不要做任何危险的事情。好吗?”
甘婧这次没有笑,而是郑重点点头,再次挥手与赵闽道别,快步跑入小区内。
第二天一早,甘婧一踏入办公室就感觉到气氛异常紧张。看看公司员工大致到齐,人事主管艾米站在办公区中央简短地做了一个公告:“纳士大股东赵先生很看好公司发展前景,准备借大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东风扩展纳士经营范围,拟向公司再次注资。一周后,赵先生委派的财务顾问将到公司考察经营情况。如有涉及到各部门事宜,请各部门领导、项目组负责人积极配合。”
甘婧面无表情地听完,低头干活儿。
下午上班前,甘婧看到财务部的两个小姑娘从档案室里拉出一手推车的票据,气喘吁吁地进了财务室。
拉出第二车时,叫吕方舟的小姑娘语气中已经有了怨气,“什么狗屁大股东,以前听都没听说过。注资就注资,查个什么账呢。一看就居心不良。”
叫汪甜的小姑娘接道,“查账就查账好了,那个什么赵先生自己还不来,让财务顾问来,明摆着是不信任我们嘛。”
“你不知道,有钱人都是这样的。”吕方舟说。
“有钱了不起呀。有钱就能麻烦别人呀。”汪甜愤愤地说,“于娜也是的,一个人躲在房里孵空调,也不出来帮一下。”
“她不是拍房总马屁拍得好嘛,这种粗笨事情哪里轮得着她干。”
“让你们干点活,你们凑一起聊天,不想干了都给我滚。”吕方舟的语音未落,房莺一脸怒气地出现在办公区。
两个小姑娘吓得脸色苍白,连忙低头拼命拉车。
“房总,您来了就好。徐总这边有份报销单正好要您看一下。她还蛮急的。”听到房莺的声音,屈志华踩着小步从自己办公室迎了出来。
房莺哼了一声。两人一前一后进了财务室。
原本在财务室内整理票据的于娜见状,忙识相地端着水杯送到房莺手中,赶紧出来和汪甜与吕方舟一同搬票据。
光天化日,不太方便关门,两人交谈的声音便一高一低地传出。
屈志华语速慢,说起沪语来甘婧也能听得八九不离十。房莺的话则是半蒙半猜。
“公司经营情况这个样子,徐总还不收敛点。”房莺声音低沉。
“何总不管,您也别管这么多吧。”屈志华慢慢地说,“女人操心太多容易老,下次见面,我儿子就没办法叫你姐姐了。”
财务室内,房莺终于忍不住笑了一声,“小赤佬!”
看看气氛缓和,财务部三个小姑娘这才结伴回到房间。坐在甘婧旁边的蓝祖平叹了口气,低声说,“伴君如伴虎啊。”
甘婧笑了笑,没敢接话。
这天晚上,财务部与行政部破天荒地留下加班到晚上十点钟。
财务室内,屈志华下班后,房莺又恢复了冰冷的表情,三个小姑娘吓得哆哆嗦嗦,大气也不敢出。
行政部内,负责档案管理的行政人员胡粉花将近两年的档案全部摊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一份一份认真审查,缺签字的、少公章的、没日期的、金额不详的全部挑选出来,待房莺过目后,想办法补充完善。
一周后,受大股东委托的财务专员来到纳士公司。因为何其多仍在美国处理家事,纳士的接待和配合工作全部由房莺和桂望国负责。
何其多专用的总经理会议室被临时布置成接待室,听汇报、看材料都放在那里进行。
五名来自全球知名财务公司的年轻人一出现在纳士的办公区,就引来一片小小惊叹声。与纳士员工的随性自然相比,这五名财务专员全都像是从制服广告中走出来的模特,男女均着剪裁合体的深色制服,头发整理得清清爽爽,脖子上挂着印有个人照片的工作证。
待审计工作真正开始后,纳士员工发现,这五人尽管外貌穿着与自己差别很大,但工作性质其实相差不远。他们也要对着那些与计算机代码同样枯燥无味的数字,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
在茶水间,甘婧听到两名财务审计人员短暂对话,一名外型丰满的女孩细声细气地说,“我这个月又胖了十斤。医生说,男人加班会瘦,但女人却会胖。因为内分泌失调了嘛。”
旁边一名卷发女孩小声说,“胖怕啥呀,我心脏这几天一直老痛咯,刚想去看看,就接了这个Case。侬听说哇,前天,一位师姐过劳死了。说是劳累过度,又没时间休息,最后小感冒转成了脑膜炎。”
“伊拉今年多大?”
“二十六岁。还没结婚。”
“老残酷咯。伊拉爷娘岂不哭惨了!”
“是滴呀,白发人送黑发人,伊拉爷娘花嘎许多银子才将她供养大,还没看着她成家立业,人就走了。”
“所以说,有病一定要看医生,千万不能拖。”
两个女孩子对望一眼,眼神中全是惶恐。
甘婧听得心头一阵发冷,端着茶杯快步走了出去。
这项名为经营情况调研,实则为财务审计的项目没日没夜进行了整整十天。
十天后,房莺与桂望国设宴欢送五人离开。目送五名脸色晦暗、但衣着发型仍然丝毫不乱的年轻人离开,甘婧在心中暗暗祝福,希望胖女孩不要再胖了。那个说心脏一直痛的卷发女孩有时间就去看看医生吧。
房莺和桂望国宴客回来时,甘婧偷窥了一下房莺的表情。她隐藏在眼镜后面的目光闪烁不定。让人看不出她内心的喜忧。
这女人,哭和笑都是一个表情。甘婧在心中暗想。
财务审计人员离开的第二天晚上,赵闽在马来西亚给甘婧打来电话。
“这里和上海有一个小时时差,你休息了没?”手机那端,隐隐传来沉闷的海浪声。
此时,甘婧仍然在办公室加班。听到赵闽的声音,她有些惊喜地说了声还没休息呢,将手机紧紧捂在耳朵上,快步走进消防通道。甘婧来不及客套,先低声将审计人员的工作情况向赵闽描述了一番。
听说审计人员已经离开,赵闽只是淡淡哦了一声,转而轻声问道,“你最近都好吧?”
甘婧回答了一句老样子,接着扭转话题,“他们何时能给你出审计报告呢?”
赵闽说,“大概后天就可以吧。”
甘婧对着电话那头点点头,“如果报告有什么问题,您方便告诉我吗?”
赵闽笑,“当然方便呀。”
说完这句,两人竟然无话。
沉默半晌,甘婧小声说,“没什么事,我就先挂机了。”
赵闽说好,在甘婧挂断电话前,他又追了一句,“有事的话,记得打我电话。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
甘婧说好,又等了一会儿,见电话那边再无声音,才默默挂断电话。
心情略显复杂的甘婧没发现,就在她接听电话时,有个人影一直站在消防通道门后,悄无声息地注视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