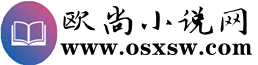上京城南,一所破败的宅子。
正屋的大门紧闭,屋中干燥的灰尘味道中,含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腐朽气息。
污迹斑斑的地上,跪坐着一个被缚住手脚,蒙住双眼,口被一团布堵住,正在极力挣扎的妇人。
妇人衣着花哨艳俗,衣料廉价,面上的厚重妆容也掩盖不了岁月刻给她的痕迹,这是个被生活磋磨过的女人。
一名著黑色劲装的男人上前,伸手取下蒙住妇人眼睛的黑布条,女人瞬间停止了挣扎。
女人试图睁眼,但长时间的黑暗让她不能迅速适应突然的光亮,哪怕屋中的光线较为昏暗,她仍因眼睛的刺痛,无法完全将眸眼睁开。
她闭眼,又睁眼,反复几次后,才慢慢适应了周围的光亮。
待她仰头看清了立在她面前的两名黑衣男人,女人反射性地往身后一缩,扭着有些粗壮的身体挣扎。
“唔……唔……”
一名黑衣人走至女人面前,半蹲下,冷冷开口:
“警告你,不要吵闹。”
黑衣人伸手扯掉堵住妇人口中的布团,女人的求救声立马响起,
“救命啊!来人呐,救命……”
“啪”的一巴掌,女人摔向一旁,同时也止了口中的惊叫。
男人一手将女人提起,让她重新正起身,再次警告道:
“闭嘴。”
女人左脸微微肿起,连连点头,而后小声地哀求道:
“你们,你们不是说放我回去的吗?你们又绑我来作甚,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千真万确,我发誓,若有隐瞒,我天打雷劈。求求你们放了我……”
“把你之前说给我们的事,重新再说一遍。”黑衣男人冷声道。
“我说,我说。”女人连声道。
女人瑟缩着身子,微微有些抖,此时她已看清周遭的环境。
在这个残破不堪的屋子里,她前面几步之外那道帘子后,似乎还有一个男人,她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见那个男人脚上登的黑靴。
她明白,这些人让她再说一遍的那事,是说给帘子后那人听的。
女人没敢过多犹豫,说一遍是说,说两遍也是说。
她畏惧这伙人凶残,当初那么多年前的过往,都查到她身上,她不敢不从。
女人思索片刻,可是絮絮述说,
“奴家名叫花玲,也有恩客叫奴家玲儿……”
“嘭”的一声,是一个黑衣男人一脚踢向身旁的椅子。
女人身体抖了抖,重新开口:
“奴家,奴家在千水长廊的花名叫花玲,奴家的本名叫做,叫做牛菜花。”
“奴家原籍荆州善郡定陶镇……”
“说你同秦四爷什么关系。”男人不耐地冷声打断女人的话。
“秦四爷……”女人面上缓了缓,
“奴家曾是四爷的姬妾,奴家同四爷是在千水长廊相识,四爷待奴家极好,奴家从来没见过这么大方的恩客,许是喜欢奴家这把好嗓子,四爷还替奴家赎了身,四爷他……”
“说你为何从秦四爷那里离开。”男人打断女人跑偏了的回忆。
花玲余光瞥了一眼帘子后的男人,
“四爷将我赎回去后,每晚都宿在我那里,当然也是一番温存,四爷啊……”
“嘭”,又是一声,那名黑衣人又踢了一脚椅子,似是已很不耐烦。
花玲身体又颤了颤,接着说道:
“那也是一个冬天,奴家记得很清楚,那夜四爷没来找奴家,奴家有些受不住,这女人哪,一旦尝到那滋味,也同男人一般,会上瘾的……”
触到对面男人冰冷的目光,花玲赶紧转了话头。
“我起身寻去四爷那里,在路上远远看见一个女人进了宅子,那女人用一身斗篷裹住了全身,但我哪儿分不出啊,那走路的姿态,那身形,铁定是个女人。”
“女人进了四爷房里,还关了门,门外守着下人,我没见着屋子里的情形。但我知道,四爷有新欢了。”
“我没有吃味,男人嘛,哪儿能指望他们一辈子只喜欢一个女人,我只希望四爷能偶尔来来我这儿。”
“但接连几日,四爷都没来,但我每日都会看见那个裹着斗篷的女人,去四爷的屋子,还是白日里来,待两个时辰就会离开。”
“我就明白了,白日里,还兜着斗篷掩人耳目,这铁定是偷情呢。”
“四爷那活儿厉害,寻常男人不能比,那位,指不定是哪个官家夫人,自家老爷不行,偷着出来尝尝滋味。”
“后来,有一夜,那女人又来了,守门的下人不知为何离开,我见机会终于来了,我也是好奇,赶紧过去,一推门,门竟然没栓,我估摸着是四爷的情趣,不栓门才更刺激呢。”
“我推开一点门缝,果然啊,床榻上赤条条叠着两段身子,正在翻云覆雨,榻上的情形尤为激烈,看得我心痒痒,四爷都没对我那么勇猛过,果然是偷的更让男人亢奋呢。”
“这回我还看到了那女人的脸,那女人我见过一次,她来过四爷这里,不过是白日里,在正厅谈生意。”
“你们猜是谁?哦,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女人又撇了一眼帘子后的那双黑靴,继续道:
“是当朝右相,秦相爷府中的贵妾,宋眉。”
话落,一帘相隔之后的那张椅子上坐着的男人,面色黑沉地骇人,紧扣住椅子的双手,青筋暴起。
花玲的声音继续在屋中响起。
“我不敢待太久,只看了几眼,就赶紧回去了。”
“第二日,那女人又来了,她似乎胆子更大了些,进了院子,她便放下了兜帽,这回我看得一清二楚,就是秦相府那个宋眉。”
“四爷亲自出来迎那个女人进门,四爷揽着那女人的腰身,我一见宋眉那细腰的轮廓,再看看我自己的腰,自己似乎是没人家的弱柳扶风,难怪四爷喜欢地紧。”
“啧啧,听说这宋眉已经生过一个女儿,这生过孩子的女人,还这么有行情。”
“四爷可是秦相的四叔啊,这偷情,还偷到自家侄子头上了,还是位高权重的相爷。”
“这我便服气了,那滋味,可不必再我身上的得劲?”
“我见四爷的心思都到他那侄儿媳妇身上去了,而且这么大一桩丑事,我住在那宅子里,指不定哪天四爷怕东窗事发,将我灭了口。”
“我给四爷说我害了痨病,让四爷放我离开。”
“四爷心思不在我这儿,但可能对我还有几分情意,给我一笔钱,就放我走了。”
“我拿着那笔钱,去了豫州。”
当然,花玲又入了花街柳巷,重操旧业。
花玲这话头一上来,就收不住,继续说道:
“后来听说,宋眉还生了一个儿子,秦相爷可宝贝了。”
“也不知宋眉那个儿子,是秦相爷的,还是四爷的。”
“那秦相爷也是可怜……”
------
黑衣男人转身进了帘子后,向坐在椅子上的锦袍男人道:
“相爷,还有什么要问吗?”
跪坐在地上的花玲瞪大双眼,她似乎听见那人唤了一声,“相爷……”
莫不是……
花玲就着仍被绑着的姿势,当即向地上磕着头,
“相……老爷,老爷,我没对别人说过,一次都没说过,就算我说,这谁信哪,这事儿我保准儿烂在肚子里。老爷……”
帘子后的锦袍男人起身,一步步走了出来。
花玲没有见过秦相,但她在风月场上,也见过不少达官贵人,她心能确信,面前这人,应是非富即贵。
秦文正看脚下的女人,冷声开口:
“将这人留下。”
黑衣男人顿了一下,不过主子交代了,这事儿他们不参与,让秦相自己看着办。
男人颔首,带着人离开。
屋子中只剩了秦相,和地上的女人。
花铃仰头看着这个气质儒雅,但神色冷厉的男人。
她人老珠黄,姿色不再,花玲可不会异想天开觉得这个男人是看上了她,要同她云雨一番。
花玲被男人冰冷的眼神看得全身直冒冷汗,她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
而男人收回眼神,抬步出去。
不多时,另一个像仆从的人进来,从袖中取出一张白色巾帕。
花玲瞪大双眼,不待她反应,男人快步过来,将巾帕捂住花玲的口鼻。
“唔……唔……”
花玲挣扎了几下,就双目圆睁,身体慢慢软了下去。
张全取回手帕,见女人唇百边开始淌血,张全伸手试了试女人的鼻息,而后起身出门。
------
秦文正立在门外的廊下,看着院子中的一片萧索的景象,心中寒凉。
张全出门走到秦相身侧,
“相爷,人没了。”
秦文正姿势没变,冷冷道:
“处理干净。”
“是,相爷。”张全躬身道。
对今日所见所闻,张全也是很是极为震惊。
张全心中一叹,这么多年,难保这个女人已将此事告诉了旁人,此时了结她,也不过是相爷勉强拿她撒个气。
不知往后府中,会是怎样的光景。
------
秦文正出了那所破落的院子,抬眼看了天色。
今日天气阴沉,索性还没下雨,但也没有一丝暖意。
秦文正上了马车,马车径直向北,驶往大理寺。
今日大理寺的大牢,会发出一批押往岭南的犯人,这里面,也包括秦四爷。
秦文正到达大理寺时,正好碰上押送的队伍准备出发。
队列里带着镣铐的秦四爷,一眼见到下了马车的秦文正,像见到救命稻草一般,疯狂地想要冲过去呼喊道,
“文正,文正……”
秦四爷被押运的官兵拦住,领头的军士认出了秦相,当即走到两三丈之外的马车处行礼:
“秦相爷。”
秦文正颔首,朝押送队列那边淡淡地扫了一眼,而后从袖中摸出一个荷包,递向面前的军爷。
“相爷,这……”
这位军士其实明白,犯人的家属向他们打点茶水钱,是惯例,而他们也都是笑纳了,上头也不管他们收这点辛苦钱。
秦相对面前人道:
“给兄弟们添点冬衣,这么远的路程,一路辛苦。”
“我代兄弟们谢过相爷。”那个军爷躬身双手接过荷包。
秦文正又看了秦四爷一眼,对面前的军爷道:
“秦四爷,是本相的四叔,他经此一遭,也不知熬不熬得住。”
“他极可能会想不开,路上遇上江河,经过悬崖,路过毒瘴,你们多看着点。”
“假如四叔真的没了,劳烦你们给他置办一副好一点的棺材。”
“是是是,相爷。”那个军爷连连点头。
秦文正双眸微眯,盯着面前的军士,一字一顿地开口:
“你记住了?”
“记住了,记住了,相爷……”那个军士连声道。
但他突然反应过来什么,震惊地抬头,同秦相一双冰冷的眸子对上。
军士心中一惊。
这……
他们时常会收到犯人家属的打点,里面不过就两种意思,要么活,要么死。
秦相爷的意思是……
------
秦文正满意地看着军士的表情变化,抬步越过他,走向秦四爷,在离秦四爷两步远的地方停住。
秦四爷见秦文正终于过来,痛哭流涕,
“文正,文正救我,我错了,四叔错了,四叔对不起你,四叔对不起你,文正……”
谁也不知道,秦四爷这声对不起,说的是败光了秦文正的家业,又还是睡了秦文正的女人。
秦文正冷冷看了秦四爷一眼,没留下一句话,转身离开。
待秦文正的马车消失在街角,那个官兵打开锦囊,里面竟是一包金叶子。
他此刻万分确信,秦相爷,就是那个意思……
这是……
买命钱……
第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