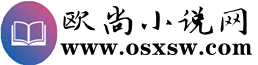“不认识。”容越恨恨的说了一句。
上官文慈撇嘴,不认识就不认识,好像别人欠了你几百万两似的。她看向楚莲若,“我来这里是想要问问这施玉音又跑来做什么?”声音有些没好气,“怎么?是不是嫌我打扰了你恩爱啊?”她倒是笑眯眯的。
楚莲若翻了个白眼,这个动作,今日似乎做了许多次了,“来了正好,这位闲的无聊的人来给咱们送线索来了。”
话题再被绕回到了容越的身上。
这一次,容越可是不敢在推辞了,瑟瑟的看了一眼风轻,恶狠狠的道:“我为了寻酒晃悠到了宰相府的时候,发现其中的守卫一点都不严密,但是出乎意料的,我循着酒香找到酒窖的时候,竟然被包了饺子……”
当日,他在宰相府里寻觅了许久,终于让他发现了酒水的藏身之地,可是凭着他的轻功,进去那间荒废了许久的院子的时候,却被一群好手给围攻了!
本来拼着重伤逃走也是不成问题,但是这里明明是酒窖,而据他得来的消息,宰相府虽然有好酒,但是宰相本人却并不是好酒之人,因而这好奇心一动,他便将计就计的被俘虏了。
“于是,你遇上了谁?”这才是重点,可惜容越似乎是在记恨刚刚的仇,硬是将旁门左道的功夫说了许多,才回归了正题。
“莫要着急,这就说到了。”容越挑了挑眉,示意楚莲若耐心,“我为了保存体力,更是为了以后的逃亡,便直接假装昏迷……”
不出预料的,他被带到了满是酒香味的房间!
在一阵耳语之后,他身边便陷入了安静,身上的绳子依着奇怪的方式打了结,自己的穴道也被封了,只是旁人不知他的本事儿,以为封了穴便可以放心了,却不知他还会移穴。
就这么一个疏忽,才有了他后来的发现。
他安静的在地上配合的躺了一夜,第二天有人过来查探他的情况。
容越赶紧调整自己的呼吸,让人看不出任何的异常。
“主子,还是昏迷。”有人蹲下来探查他的脉搏与呼吸。
他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似乎是特意压的沉沉的嗓音,“可查出了是谁?”
那个一开始叫主子的属下,蹲下了身子,在他身上胡乱摸索了一通,继而他听到自己腰间的佩玉被扯了下来。
然后那个主子便沉吟了一会儿,“柳叶山庄的庄主最是爱酒,怕是来寻酒的,便让他昏着,只要不找到我们的秘密,便也莫要了他的命。”
估计是怕麻烦,毕竟与武林上的山庄结为仇人,这绝对是个不小的麻烦。想不到这个身份还有些用处,关键时刻还能让人忌惮忌惮。
只是秘密……是什么?这里,果然反常必有妖!
当两人离开的时候,他缓缓睁开了眼,扫视了一圈,但是却还是冷静的躺在原地,他不能确定暗处是否有人听着看着。
如此又过了一天,他计算着时间,直到已经入了夜,谨慎退去,当他利索的将绳子挣断的时候,他听到了一声比猫咪浅叫还要轻的哽咽声。
没有任何的其他想法,循着声源,直接找到了一个暗室,“是谁?”
“救我……”那道轻微的哽咽声,似乎突然惊颤了一下,旋即便是一道尖锐的求救声。
容越心知,这里关了一个少女,且是一个妙龄少女……也不磨蹭,伸手就招呼上了这暗室周边的机关,几个回合的摸索,‘轰隆’一声,严丝合缝的石门就这么打开了。
他一个闪身,便跃了进去,一眼便扫视了暗室内的场景,什么都没有,对,除了一个人,什么都没有。
而这个人身上,除了简单的中衣之外,也是干净素雅的非常。
暗室很暗,只有西南角的高墙上露出了三个拇指大小的洞,只为了让缕缕的光芒透下来,其上似乎还封盖了什么透明的东西,防止刮风下雨或是漏下来什么。
“救我。”角落里的人抱着膝盖,在他进来的时候,目光灼灼的似乎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最后的救命稻草。
容越这个时候的好奇性子又一次的冒了出来,“我为什么要救你?”
仅仅着了中衣的女子则是扶着墙缓缓站了起来,“我是伯阳候的女儿,你若是救了我,想要什么,我爹自然会给你,他最爱我了。”沙哑的声音已经不复尖锐,似乎是在这里关了太久,刚刚那一瞬间听到来人时的凌厉只是求生的本能,如今却也逼着冷静了下来。
容越暗中点头,这女人不错,至少还能冷静下来,而不是一味的去哀求,还知道允诺他条件,也知道此时表明身份才是最简洁明了的保障。
他能够不受控制的走进这里,且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看着这方天地,必然是被掳之人,那么即便此时救不了她,凭着这份不受控制,有朝一日说不得就逃了出去,而她在这里的消息或许会不胫而走,到时候,可由不得宰相再关着人。
只是点头归点头,认可归认可,他却突然意识到了一点,“你是伯阳候的女儿?”
女子一再的点头。
“你可知道,如今伯阳候的女儿正在皇帝的储秀宫里,若你才是,那她是什么?”容越毕竟装了一两次萧风,因而对于后来他们的怀疑也做了些微的打听。
所以知道林月的存在。
暗室里就这般沉默了下来。他意料之中的歇斯底里没有,这个女人倒是好强的接受能力。
许久许久,直到容越打了个哈欠,打算就此打道回府顺便做个顺水人情将这事儿给说出去的时候,却听她缓缓言语:“进了皇帝的储秀宫么?父亲一定伤透了心吧!”
他不直到为何这声音陡然变得凄凉,却因为那一份对着父亲的歉意听进了耳里。而就是这一份歉意,让容越生出了带着她一起打道回府的心。“跟我走。”
“你真愿意带我离开?”似乎这个消息令得女子太过惊讶,三步并作两步就想要跳过来,却发现长期待在这间屋子里的她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这个对旁人来说很简单的动作。
容越眼瞅着女子摔倒在地上,却并没有去扶。
而这位自称为伯阳候之女的人儿也不矫情,更不在意,有人说了带你走,于她而言已经是一种天赐的恩泽了!
她挣扎着重新站了起来,这次倒是没有急于求成,而是一步步的走近了容越。
容越眯了眯眼,至少还能走,倒是不算带个废人。抬头看着那三个小孔,却发现这个夜晚,星辰闪烁,还算是亮堂。这样的环境,最不适合逃离。
容越改变了想法,“明日再走。”
伯阳候之女自然不会反对。
“你怎么会在这里?”沉默下来,便无趣了,他挑了个话题。
“我三月出游之后,在画舫上睡着了,醒来便在这里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更甚至,我都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她的眼神有些颓废,但是眸中倒是韧性十足。
“这里是宰相府,三月!宰相好能耐啊。”三月正是皇帝选秀的时候,被关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屋子里半年多,若是一般女子或许早就疯狂了,这人也是个好耐性的。
“你说这里是宰相府?那么送进宫的一定是宰相的人?父亲,父亲会不会被连累……”一下子本来安静的言语的女子便闹腾了开来。
容越听得心烦,手上一动,就点了她的哑穴。
“冷静了就眨眼。”容越虽然不是坏人,却也别指望他做了那老好人,这女子与他本就是萍水相逢,愿意救是他心情好,不愿意救是他本分!
女子大喘了好几口气,终于将自己的心绪给压了下去,才给容越眨了眨眼。“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容越摆手示意无碍,“你老爹没事,但是最近宫中的事情可不小啊。”
“怎么说,是不是跟我有关,跟……那个假的我?”她还算是小心翼翼的问道。
容越也不吊人胃口,倒是一五一十的将所有的一切都说给了这位面上强自镇定的女子。从淑妃遇害,楚莲若与上官文慈中毒,再到这些天所有人调查的方向一桩桩一件件,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竟然说的一滴不漏。
这屋子里没有桌椅,容越立在一边,随意的靠着墙,那姿态,就是个说故事的人。他看不清这真林月的表情,也没有那个兴致去看清。
将所有的一切说清楚,他难得的听到了女子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
“你究竟是谁?”没想到,这林月倒是没有怀疑这些事情的真实性,而是反过来问他究竟是谁?
其实很简单,若是一般的人,怎么可能得到如此详细的皇宫秘闻?
“我是谁,你没有必要知道,总之这案子,我也搀和了一脚,而且是作为主动方。”容越撩了撩衣摆。
林月后退了两步,从洞口漏进来的月光,招不大清容越的脸,尤其是他还故意的站在了阴暗的地方。
有些戒备,因为他提到了主动的一方,那么这主动点的一方,究竟是查案的人,还是下手的人?
容越嗤笑一声:“不用戒备我。”也不解释,顺着墙壁盘膝而坐,此时倒是需要蓄存好体力,若不然,今夜若是有人闯进来,怕是一场硬战。
不过到时候,真到了生死存亡,他也不会去管这个女人。
人性本就自私,谁也不能说什么?
幸而,这个夜很安静……
天亮了之后,容越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勾了勾手指,早就醒了的真林月便也站了起来,许是吸取了教训,她起来的动作不快,大概是要给自己习惯的时间。
容越倒是好耐性的等了一会儿,之后估摸着时辰差不多了,便向外而去。
只是在门口的时候,他顿了顿,如果就这么出去,一定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因为此处的戒备竟然比之前还要严了许多。
虽不是铜墙铁壁,但也的确更麻烦了。
正当他敛目沉思的时候,他透过狭小的缝隙竟然看到了一个熟人。
林月是大气都不敢喘的看着容越的背影,突闻低沉的嗓音响起,“待会儿,我一打开门,你就冲出去,什么废话都不要说,就说自己是林月,大呼自己是伯阳候之女……”
容越的声音不容置疑,林月正是六神无主之际,自然他说什么便是什么?
于是,当石门,被容越暗暗打开的时候,林月倒是胆子大,完全的遵从了容越的说法,说起来那叫一个奋不顾身。
“你们是不知道那女人多疯,我看的都全身发麻!”容越夸张的抱了抱手臂。
“你遇上的熟人是萧风?”楚莲若自容越说道真林月的存在竟然在宰相府的时候,那一张脸便一直沉着,胥阳安抚性的按了按她的背脊。
那意思是告诉她,不用担心。
容越并不否认,只是转而从自己的衣袖里掏了掏,“我还发现了这个!”
那是一叠暗黄色的锦缎,其上绣了红黑花纹,没有什么不对。
只是胥阳和风轻看到这锦缎的第一时间就坐正了身体,楚莲若若是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这锦缎有异样,那她可真是白活了一世。
“这宰相府可真不简单,竟然奢侈到在残纹丝娟上做文章!”风轻朗然笑笑,口中说的慢条斯理,眼角却是凝着这方锦缎。
“有见识。”容越晃了晃,胥阳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他的见识可绝对不浅,老头那儿就有一方这块丝绢,据说还是胥阳送的。
“别卖关子。”果然胥阳最是干脆,只是谁都不知,他只是不想要楚莲若太过好奇罢了。
容越伸手掏出火折子,点燃屋内的蜡烛,再拿来火盆,将烛火燃起,之后就将这方锦缎直接扔在了火盆里。
楚莲若一惊,却被胥阳捉住了手,“你且看着,这锦缎其实还怪好玩的。”
听着胥阳口中好玩二字,容越有些想要打人的冲动,可是上一次之后,他便知道了,这位便宜师兄,他根本就打不过。
楚莲若和上官文慈目不转睛的盯着火盆,果然发现,那里面的锦缎一点都没有烧坏的痕迹,反倒是其上的红黑绣迹缓缓的软了下去,之后竟然隐隐出现了层层字迹。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没有人会把锦缎朝着火盆里丢,毕竟布匹哪儿有不怕火的,偏生有那么一些特例,却毕竟是让人认不清面貌。
“改天,我送你一件衣裳。”胥阳见楚莲若的眼中露出欣赏的意味,一点都不心疼的说道。
容越大呼胥阳怎么就如此败家呢。
要说这锦缎是因为当时林月吸引了萧风的注意力之后,一切顺理成章的被本来偷偷摸摸前来的萧风揪住了线索,偏偏,想要杀人灭口,却又得知萧风来此,虽然看着像是暗的,可是明面上却有许多双眼睛看着他走进的宰相府。
于是,宰相必须出面,至于怎么澄清,怎么辩驳,那都不是他管的事情了,趁着无人在意,他偷偷的溜了。
但是虽说他是自愿留下来当俘虏的,但是怎么着也饿了渴了一天一夜又半天,不想就这么空手离开。
而且,他很好奇那个低沉黯哑的声音明显是个年轻人,而据他所知,如今的宰相府可没有一个年轻人。
于是,本着来一趟,便是解不开你的庐山真面目,也得先入了这此山才行,这才有了这方锦缎的由来。
风轻张开的口,因为胥阳的声音而重新闭上。
火盆里的火燃尽,楚莲若接过卿卿送上来的锦缎,完全也不去问这算是锦缎半个主人的容越,不过幸而他也不是那纠结之人,否则这里可是有两个男人可以无声无息的将他给解决的。
胥阳微笑,这其间的秘密倒不是什么大事儿,宰相一直都不安分,有些谋朝篡位的秘密才算是正常。
若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所谓皇帝的舅舅早该从宰相的位置上下来了,而不是仅仅处置了他的女儿。
却是没有想到,这一方锦缎上的秘密,牵扯到的是身边的楚莲若,那瞬间涌现而出的恨意,让屋子里的人霎时间感受到了压迫。
楚莲若灿若星辰的眸子里如今只剩下狂风骤雨,纤长的双手,因为用力而泛出了比之白皙还要渗人的苍白,锦缎更因为她手上的力道而皱的不忍直视。
胥阳第一时间感觉到了楚莲若的异样,想要一把夺过楚莲若手中的锦缎,却因为她抓的极紧,而无从下手。
若是他强行为之,遭殃的便是楚莲若的指甲。
“若儿,有什么跟我说,有我,不怕!”只得一遍一遍的唤着她的名,只得一遍一遍的摩挲着她的手,让她缓缓的放松。
“我要宰相从此再无翻身之地。”楚莲若机械般的转首,对上胥阳的眼,一个字一个字的,若珍珠落地,掷地有声。
却不啻于一道闪电,将山峰上高耸的植物狠狠的摧毁一般,风轻眯起了始终不打眼底的笑意,上官文慈收起了眼底的调侃,而容越愣怔了许久。
这样的女人,或许他知道自己这个被老头说的好上了天的师兄为何会看上这样的女人?
所有人眉眼之中各有所思,而从未见过楚莲若这般的胥阳,愣了愣,却也在转瞬,重重的点头,“好!”
似乎楚莲若的所谓意见,胥阳说的最多的便是好。
楚莲若的手缓缓放松,锦缎被胥阳见机直接扔在了一旁。他拉着楚莲若,狠狠的拥入了怀里。直撞地自己胸口生疼,但是他不在乎,他不喜欢这样的楚莲若,不喜欢这样阴冷的楚莲若,不喜欢这样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楚莲若……
所以他的动作有些粗鲁,甚至他听到了楚莲若的闷哼声,但是这一刻,他没有松开受伤的力道,甚至双臂收的更紧,更紧!
那张锦缎上写的是秦老将军当年被诬陷的信息来往。果然,楚莲若一碰上秦老将军的事情,不论是情绪还是身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楚莲若没有挣扎,她埋首于胥阳的胸膛里,只觉得浑身阴冷。
他父亲的身死,竟然还有宰相的参与,是啊,本以为今生她的仇人不过是施玉音和胥容二人而已,可是因为胥阳的关系,她接触的越多,才发现自己秦家的人竟然牵扯到了那么多的人。
先是琉璃寺苏王之祸,再有宰相府的两面三刀,尤记当年,秦老将军,每次总是喃喃着,这京都还是宰相府那个老东西能够与他下棋杀个痛快。
却原来一切都不过是表象而已!
“胥阳,胥阳,我只有你了,今生只有你了……”楚莲若突然低低的呢喃,合着泪水淌在他的怀里,直直的撞击在胥阳的心底。翻腾的情绪涌动的太快,楚莲若根本就无法宣泄,除了紧紧的搂着胥阳之外,她想不出任何办法。
他一手扣住楚莲若的后脑,以头摩挲着楚莲若的脖颈,“我会一直在,一直都在!”原来他的若儿将他看的这般的重,如此的独一无二,胥阳心中又是欣喜又是心疼。
风轻的眼神只是轻轻落在二人的身上,便收回了,起身,抬步,再没有回头,背影却是含着层层的落寞。
容越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叹息,却二话不说,抱上还在惊愕之中没有回过神来的上官文慈抬脚便走。
素容怔然的看着如此肆意的容越,突然反应过来,自家主子被另一个男人给抱走了。
怔然归怔然,她立刻便跟了上去。
而上官文慈却是瞠目结舌的看着这个不过一面之缘的男子,江湖儿女本就没有多少在乎,所以她也没有惊呼。
大眼瞪小眼的看着容越,“你究竟是谁?”
“还记得,那一日与你瞪眼的萧风?”容越在门口定了定,等着素容出来给他带路,他还不知道上官文慈住在哪儿的房间里。
“怪不得,我总觉得奇怪。”上官文慈撇了撇嘴,“你怎么就把我抱出来了?可是那一日对我一见钟情了?”她骨子里的恶趣味儿被如今稍稍有些明朗的局势给带了出来。